《2020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健身门店总数达到4.43万家,国内健身参与者人数从2019年的6812万人增长至7029万人,健身人群渗透率为5.02%。 (视觉中国/图)
经过长期节食减肥,当暴饮暴食的闸门打开时,心月最喜欢的食物就是坚果。
含油量高的小坚果最容易满足长期不吃油的人。 馨月将其描述为一种对大脑神经系统的刺激——只要嘴一放到上面,就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有一次,她吃了数百颗坚果。
24岁的新月是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硕士生。 初三的时候,她的体重达到了240斤。 高中时,欣悦靠节食和减肥药减肥到140斤。 她还尝试了众多市面上流行的减肥方法——哥本哈根饮食、21天禁食、中草药套餐减肥等,成功减重至130斤,并且还出现了反弹。 。 大学期间,她沉迷于健身房,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在40度的高温下疯狂做“举铁”和“健美操”。
但心月却发现自己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功利性地追求健身效果,并没有享受到运动的乐趣。 她总是在别人的注视下,却从未掌控过自己的身体。 这种对身体的压迫,在2017年10月引发了反弹,心月陷入了暴饮暴食、呕吐的深渊。
在《肉身的创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中,馨月描述了肥胖者生活在身体焦虑中的心态。 “以前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对自己的饮食感到愧疚,不惜向自己的身体发动战争——节食、过度运动、呕吐……在经历了减肥和反弹的反复折磨后,我留下的只有疲惫和深深的感情。 深深的自我厌恶。”
《肉身的创造》汇集了华南师范大学运动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欢及其学生深度采访的12位中国健身女性的故事。 其中包括经历过“暴饮暴食”的肥胖者、离婚的中年职业女性、移居城市的“打工妹”以及准备怀二胎的老年妇女。
在本书编写的三年时间里,“白瘦儿”、“马甲线”、身材焦虑等问题日益受到舆论关注。
“这里的身体不是纯粹的物质身体,而是物质、社会和精神混合体的统一体。” 熊欢写道。
在最近的播客中,熊欢分析了女性身体焦虑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她认为,东亚社会尊重白、瘦、年轻,因为“男人最喜欢白、瘦、年轻的审美”。 在批评女性的外表焦虑时,更重要的是要澄清“是谁在构建这种性别文化和性别秩序”。
“审美是一种社会建构,人类有物种差异,无法达到统一的标准。对于肥胖来说,因素有很多,有时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因为除了自身基因之外,肥胖也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科技的介入、消费的诱惑,因此,肥胖必然是一个公共问题,“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有其自身的美感。”英国规定商店不能把糖果放在门口的政策是从公共政策层面解决肥胖问题。
《肉身的创造》中的12个口述故事,大部分是课题组成员完成的田野调查。 陈海飞,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既是研究员,也是健身教练。 2015年底,她开始在一家健身工作室担任教练。 成员主要是女大学生。 她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个年龄段的健身女性。
在陈海飞看来,除了从技术层面赋权女性身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结构层面赋权女性。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消费文化如何迫使一个人比他们需要的更加活跃,或者过度焦虑。”
陈海飞从小就喜欢运动。 在别人眼里,她非常自律。 “你是一名运动从业者,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明信片。虽然你不能看起来像模特,但你必须看起来像经过训练。这是你的专业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也是身体焦虑,因为你有我很害怕我的肌肉会流失,或者我的运动能力会下降,我会变得太弱而不能跑或跳,这也是对自律的要求。”

以下是陈海飞的说法:“太功利或者运动太多,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我曾经短期辅导过一名会员。 当时她还在读研究生。 她可能已经失恋了。 她很着急,每天要跑2个小时、10多公里,才觉得自己今天做了点什么。 她早上跑步,晚上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 她每周会和我一起锻炼三到四次。 这样的运动量即使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令人恐惧的。
除了高强度的运动之外,她在饮食上也非常克制。 为了更好地控制饮食,我还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 她会用一款APP来计算热量,将每天食物的热量精确计算到个位数。 一段时间后,她不再需要机器来测量食物卡路里。 食物不再是食物,它只是一串卡路里数字,比如一根玉米有多少卡路里,一块肉能不能吃。 它已经自动化了。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站在肯德基餐厅门口,在微信上泪流满面地问我:“能给我一个甜筒吗?就一个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陷入了贪食症的恶毒之中。 循环。 当节食达到临界点时,你会吃得过多,但这并不能解决焦虑,反而陷入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 那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哭了起来,一种歇斯底里的绝望。 我为她感到非常难过,想要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来减轻她的痛苦。 作为一名健身教练,我可以在课堂上鼓励她,倾听她的烦恼,但这些在巨大的情感漩涡面前都太渺小了。
另外一个女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川雅安女孩,中专毕业,一名文员。 在公众的认知中,健身只是白领或者中产阶级的专利。 她的经历也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患有抑郁症,但我经常听到她说起失眠和幻听的事情。 那时的她,是比较胖的。 她的收入有限,请不起私人教练,所以后来她去了一家更便宜的健身房,一个月99元的自助健身房。 它提供小组课程,你也可以自己练习。 但装备比较简单,只能满足基本的锻炼需求。 需要。 她坚持去了两三个月,当时的体重确实瘦了很多。 但由于基础重量较大,加上团体课辅导有限,练习一段时间后,我的膝盖半月板就受伤了。 减肥计划只能搁置。
当她情绪困扰时,她说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看到平时清单上列出的所有不健康食品——鸭脖、炸串或奶茶——她都想吃。 但吃完之后,她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 为了克制自己,她还加入了一个减肥群,很多人都会谈论自己的健身经历、运动打卡、分享饮食情况。
有时,她还能从中汲取力量,像打了一针鸡血一样积极生活。 当她郁闷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在努力好起来,她就会想,在这个群体里,我为什么又要吃饭呢? 她觉得自己很没用,这只会增加她的愧疚感。 这一切都成为了心理负担。 因此,运动并不总是能给人带来积极的情绪。 如果太过功利,运动过度,或者沉迷于运动,对人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大。
今天,自律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道德绑架。 当我们看到胖女孩或男孩时,我们首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如此不守纪律。 懒惰、失败等词很自然地与这个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会让我们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像这个女孩一样,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她也在考成人教育资格,希望能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她渴望融入城市,通过健身改变自己的形象,加入一些健身社区,试图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 她正在积极改变现状。 每个人的发展资源都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 在我们批评一个人不努力身材管理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男女共用的健身器材区域通常被视为男性的专属领地。 (视觉中国/图)
《健身房里的权力关系》
我现在也在商业健身房锻炼,有时候我能感受到男教练和女教练之间的细微差别。 人们可能会认为女教练技术不如男教练,没有男教练那么权威,没有男教练那么多发言权。 很多男教练都会堂堂正正地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 女教练感觉更像是在谈判,“我们这样做怎么样”或者“我们停止做更多怎么样”,这可能看起来不太有说服力,也没有那么有力。
这种对男女教练的要求和社会对男女的要求是一样的。 男性的成功更多的是基于财富、智商、地位、名誉,而女性的成功则更多的是基于外表和性格。 这是一种常见的刻板印象。 印象。 如果一个男教练忽视了身材管理,大家都会觉得他工作那么忙,成员又那么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或者是一个可以指导成员变瘦变美的人。 对于女教练,大家都会想,你这么胖还能好好指导我吗? 对男女人物的包容程度就体现在这里。

健身有不同的流派,有练健美的,有练举重的,还有人练运动能力的。 我周围不同的学校会互相比较。 比如,有些人会认为,如果你身材这么大,你就会有死肌肉,如果你整天举起这么多重量,你的身材就会走形。 对男性形象的关注大多来自于男性,比如那些体育“新手”或者非常瘦弱的男性。 他们根本不敢去实力区。 他们只敢做一些固定器械或者在跑步机上跑步。
女性对女性的目光也很明显。 我采访过很多成员。 事实上,健身房里的女性更关注女性如何练习,而不是男性如何练习。 我有一个面试成员很胆怯。 她通常在早上健身房里没有人的时候练习。 她每天盯着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女孩,看她练得怎么样,瘦了没有。 一是学会模仿,二是判断她的身体变化。 有一种暗中竞争的感觉。
有一位女成员,练得比较夸张,穿的衣服比较暴露,练得非常自信。 如果女孩在健身房里自信地练习,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感到不适。 女人会认为你不太有女人味。 男人会觉得你挑战了我的权威,占领了我的地盘。 许多人对她进行评判或对她的外表进行身体侮辱。
很多人对女性的要求就是乖巧、安静、默默地使用跑步机或者做腹部练习,不能大声喧哗。 如果你在健身房里无视别人的目光,像男人一样大方地做动作,就会被认为打破了女性气质,不遵循女性规范。 由于力量区多为男性领地,女性会员除非练得比较好或者有教练陪同才会进入。
如果一个女人自信地走进来,举起铁杆,蹲着的时候大声尖叫,举起,突破这个关卡,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她就会成为一个规则破坏者。 暗地里,存在权力关系。
我抛开研究员的身份,单独练习,因为我是健身教练,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技术方面我比较放心。 我熟悉健身房里的权力关系,这种暗流,有时我想把它搅动起来。 如果我不做研究,我就会慷慨地和一群男孩一起潜入装备区练习。 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连呼吸都变得很平静。 目光是真实的,一个女人闯入,就像一只鹦鹉闯入空间。
“本质上,对体型的要求没有改变。”
很多人说健身房是性别文化纪律的空间。 事实上,没有人规定这个领域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但这里有一道无形的栅栏。 当你在强项区的时候,当男人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占据了原本属于他们的位置,你会选择退出或者改变你的训练计划。
这种性别规训的场所是如何形成的,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我认为有三层(原因)。
一楼是物理空间。 从健身房的布局来看,除了教室和健身房有墙壁外,有氧区和力量区都是开放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教练、销售、男会员、女会员,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你训练。 只要你在这个领域,你做什么,大家都会看。
我的一位受访者说她正在健身房练习拳击。 格斗场位于体育馆的中央。 她正在上面打拳击,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她。 她明显能感觉到别人的目光,感觉很不舒服。
然后是文化空间。 如果你看健身房里的许多海报和标语,它们总是在传达着理想的体型和自律的汗水文化——你如何成功,如何不让你失望? 任何人都可以对你撒谎。 、只有汗水永远不会骗你等等,这是一种看得见的文化。 还有刚才提到的无形的性别划分,有氧区、性爱室,女会员大汗淋漓,还有男人尖叫举铁的力量区。 这种男性和女性身体的理想迫使他们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健身选择。 我们在健身房里看到海报。 男皆壮,女皆细腰。 你很少看到男人跳舞或做瑜伽。
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监控和纪律。 我们看看那些总是照镜子的人。 举起一组后,他们立即照镜子,看看自己是否练习得更好。 这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 在这个文化空间里,或者说在这个文化的影响下,就成为了驱使自己的内在要求。
健身房是身体消费行业的一部分。 身体消费包括整形、美容、身体护理。 健身只是消费文化的延伸,让身体更适合消费。 您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训练效果,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 ,符合时尚界的审美趋势,其背后还有更大的文化宣扬和宣传,什么样的身材才是理想的身材。 还有媒体宣传、广告、娱乐明星的示范效应。 我们看到很多明星都在微博上关注。 名人有放大焦虑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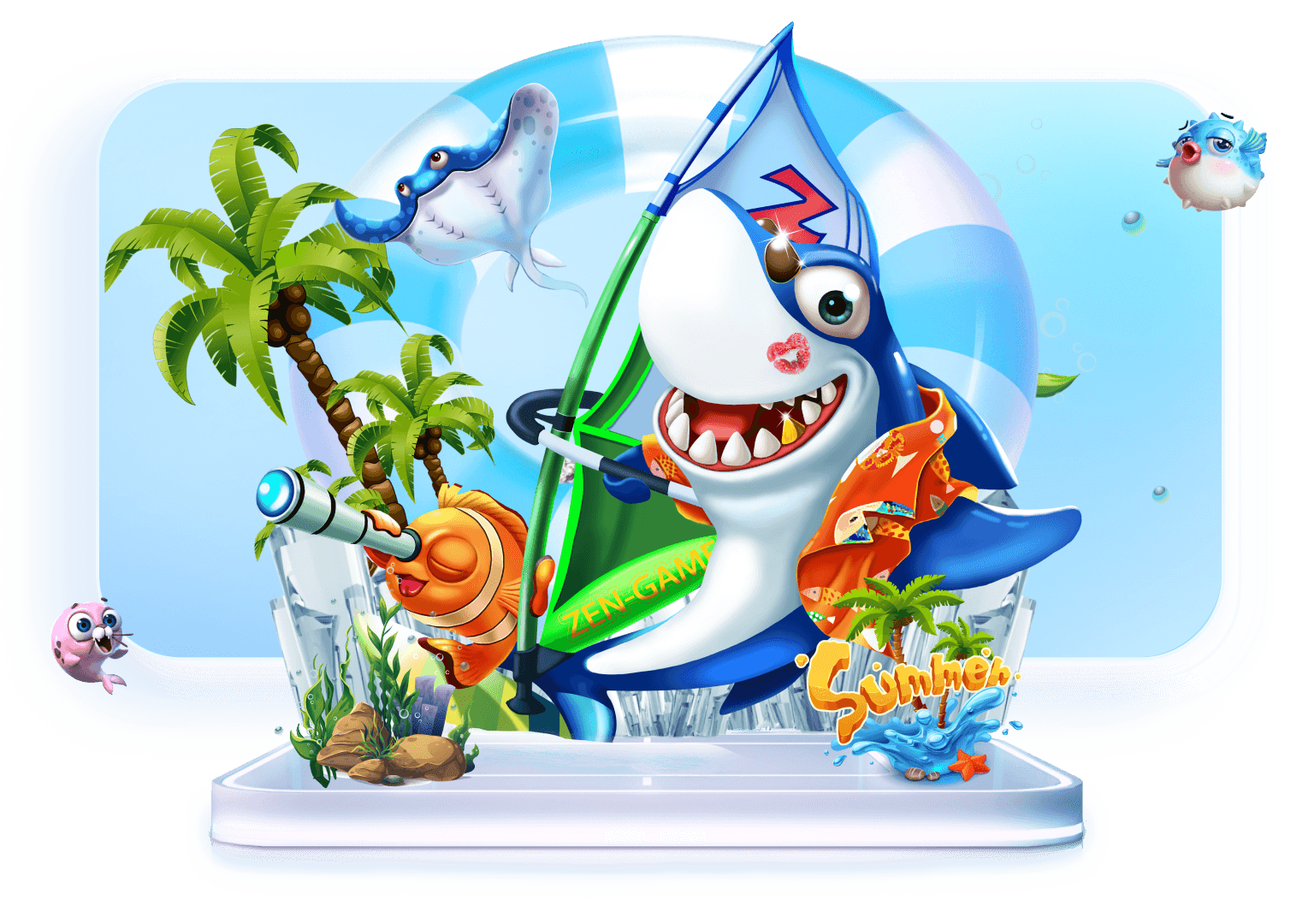
如今,我们看到BM风格非常流行,有很多国际大品牌拍摄大码女装的海报。 这当然有利于审美多样性。 但就消费文化而言,我认为它们本质上没有区别。 作为一种趋势,就是创造消费。
不用说,BM风格对女性体型有要求,但我们看到大码模特并不胖。 穿上后她还是很瘦的。 如果你很胖,穿大尺码不太时尚。 本质上,对体型的要求并没有改变。 。

1985年出生的健身女孩。(视觉中国/图)
“你绝对可以拥有和改变的就是你的身体。”
我有一个女会员,她的身材很符合国外的审美,但在中国她又壮又胖。 这就是审美上的差异。 中西方的这种差异背后,其实并无对女性身材约束的差异。 这只是文化差异。 西方推崇有胸有臀的性感女性,而中国则更喜欢苗条的女性,女性的价值仍然是根据身材来判断的。
这位成员后来出国了,因为她的身材符合西方审美,所以她更容易从一种文化跳到另一种对自己限制更严格的文化。
当我的会员来锻炼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问我一个月可以减掉多少磅。 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从生理上来说,比如肌肉含量的差异。 从文化和社会因素来看,金钱和精力也不同。 通过多年的训练,很多受访者能够逐渐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独特性,并能够辨别出理想体型是虚幻的,最终回归到自己,谁才是第一位的。
慢慢地,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这是一种认知的转变,从关注外界赋予的价值、符号、意义,回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 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文化的束缚,但它是一种和解,或者是一种积极的妥协。 我采访的很多成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通过坚持不懈的锻炼,他们慢慢回归自我,理顺社会与自己的关系。
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的能动性。 过去,人们认为人们只能通过精神和抽象思维来认识世界。 然而,具身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身体来感知、理解,反思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从个人经验来看,你完全可以通过身体活动来感受运动带来的痛苦和快乐。
我刚才提到那个女孩想吃甜筒,然后她就慢慢走了出来。 我觉得她对健身的坚持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锻炼中,她摸清了自己的身体特征:我的身体结构是这样的,我的大腿比别人粗,腰部有肉。 屁股天然有优势,稍微练习一下就能感觉到。 她慢慢的向内探索身体,向外修炼。
锻炼更像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方式。 它就像一个锚,将生命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当你感觉生活即将脱轨时,肥胖影响健康,精力下降,产生健康焦虑; 但是当你运动之后,你的身体变好了,你的能量变强了,你感觉轻松了,你就会选择坚持下去,就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累了。 如果你很急或者有很多想象力,你就会变得更加务实,根据自己的生活来安排练习。
为什么健身让你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掌控,其中有一个社会因素。 现在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风险社会。 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你可以清楚地拥有和改变的是你的身体。 比如,你今天的工作完成不了,影响的不仅是你,还有分工; 但健身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身体是我们唯一可以定位自己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心悦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付紫阳





